新興案例、勞工流動合作及其對深化區域合作的意涵

By Pooran Chandra Pandey/ Translated by Kai-Yuan Liu

「勞工流動」廣泛指的是勞動人口在一個經濟體內部,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流動的難易程度。
在經濟學研究中,勞工流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觀察作為主要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力,如何影響經濟成長與產能,並進而形塑勞動力供給的多樣性。而這又會造成工資下降,從而促成更具競爭力、較不易通膨的經濟體系。同時,也意味著在情勢需要時,能有可隨時部署的勞動力儲備。
勞工流動可分為兩類:
- 地理流動
- 職業流動
地理流動指的是勞工在特定地理位置工作的能力,而職業流動則指勞工改變工作類型的能力。一名勞工從印度移動到台灣工作,可被視為地理流動;相對地,一位汽車技工轉換工作成為航空公司飛行員,則體現職業流動的概念。
政策制定者的觀點
從政策制定者的觀點來看,地理流動可能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因為放寬移民要求可以造成數種效果,其中包括:
- 勞工供給增加:當更多勞工進入一個經濟體時,整體的勞工供給便會增加。若勞工供給上升但勞工需求保持不變,最低工資水準可能會下降。
- 失業率增加:除非雇主對勞工的需求上升,否則勞工供給的增加可能導致勞工過剩,造成失業率增加。這代表勞工人數大於工作職缺。
- 生產力增加:增加的部分勞工可能具有專業技能,如果這類勞工帶著專業技能進入職場可以增加生產力,並可能取代生產效率較低的現有員工。
獲得地理流動並非純粹的經濟議題。它也可能涉及國家主權與政府管控的問題。畢竟,政府在意安全,而完全開放的邊界意味著政府無法確定進入國內的人或物是誰或是什麼。
此外,雖然提高地理流動通常對經濟有正面影響,但它同時也是最先成為公民及民意代表的宣洩憤怒的目標之一。移民在國際上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議題,追求勞工流動政策的國家必須制定經過周密設計的措施與途徑。
「印度下一項重要的出口品在內容與規模上可能會非常不同,而最有可能的出口品就是其人民 — 屬於經濟學家所稱的『勞工流動』的一股新的、具結構性的浪潮;這股運動可能會重新塑造一個國家的經濟,以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
Pooran chandra Pandey, 2025 年外交部(MOFA)臺灣獎助金訪問學者。
印度以勞工為核心的全球勞工政策與協議
印度下一項重要的出口品在內容與規模上可能會非常不同,而最有可能的出口品就是其人民 — 屬於經濟學家所稱的「勞工流動」的一股新的、具結構性的浪潮;這股運動可能會重新塑造一個國家的經濟,以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
其概念很簡單:將印度的年輕勞工與那些因人口老化(伴隨著出生率下降)及勞工短缺而受限於成長的國家企業連結起來。這是一種對全球失衡的務實回應,但同時也是政治高度敏感的議題。儘管各國的經濟都依賴移工,反移民的聲浪卻在多國上升,並與民粹主義的元素相互交織。
這正是印度與其所在國合作夥伴所面臨的挑戰:如何讓印度勞工能夠快速且安全地跨越國界,確保他們擁有明確且安全的返鄉途徑。
概念轉化為政策轉向
印度政府現在已決定將這項概念轉化為政策。最近,印度外交部(MEA)提出了《2025 年海外流動(促進與福利)法案》,這項改革具有轉型性,旨在取代已有 40 年歷史的 1983 年《移民法》,並以此建立一套現代化的海外就業管理制度。
在不規則移民與遣返(尤其來自美國)不斷上升的時刻,安全、透明與問責成為關鍵,而法案正是以前述面向為主要焦點。該法案提議協助印度公民與「全球工作場所」接軌,同時確保他們能「安全且有秩序地返國,並在返回母國後得以重新融入」。
對印度而言,這不僅關乎海外工作,而是著眼於打造一個更強韌、更具韌性的經濟體 — 由海外匯款、全球技能,以及能在國界之外運用機會的勞工所支撐。
促進成長與流動性的機會
印度的勞動市場向來以人才穩定著稱。每年都有數以千萬計受過教育及具半技術背景的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市場,其數量遠遠超出國內經濟所能輕易吸納的程度。
同時,德國、日本等已開發經濟體正面臨完全相反的問題,包括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勞動人口降低,以及生產力停滯等情況。
這正是印度大展身手的好機會。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過去六年間,新德里已與歐洲、海灣國家及東亞多個國家簽署了20項勞工流動協議。這些國家多數擁有先進的經濟體系,但過去在聘用印度勞工方面的經驗相對有限。
其構想在於建立正式、由政府支持的途徑,讓印度人得以赴海外從事臨時性工作,從而降低常與無管制移民相關的風險與剝削。
「其構想在於建立正式、由政府支持的途徑,讓印度人得以赴海外從事臨時性工作,從而降低常與無管制移民相關的風險與剝削。」
Pooran chandra Pandey, 2025 年外交部(MOFA)臺灣獎助金訪問學者。
全球人口組成
這項全球勞工實驗的缺點在於,難以說服接收國相信移民確實是暫時的。從政治層面來看,這是一個敏感議題,因為幾乎沒有領導人願意給人留下以外國勞工取代本國勞工的印象。
「歸國與再融入」的概念,亦即移工在工作合約結束後返回母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經實際驗證。許多年輕勞工在海外發展事業或成家之後,往往更傾向於選擇留下來。
儘管如此,已開發經濟體的人口現實使這一問題難以被忽視。人口正在萎縮,退休人口壽命延長,而在義大利、俄羅斯、南韓、日本、台灣等國家,死亡數如今已超過出生數。過去對人口過剩的恐懼,正被一種新的恐懼所取代:缺乏足以維持這些經濟體運轉的人口。
現在,問題基本上在於,經濟體如何凌駕於政治與民粹主義,基於實際證據繼續運作。
僑匯巨擘
關於僑匯的數據無庸置疑,而僑匯的經濟效應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印度遍布全球的勞動人口不僅正在重塑海外的勞動市場,也在默默地支撐著該國的財政體系。根據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 RBI)的資料,上一財政年度,海外印度人匯回本國的外匯金額創下1354.6億美元的新高,較前一年成長14%,使印度連續十多年成為全球僑匯收入最高的國家,且大幅領先中國。
目前,僑匯已占印度經常帳總流入的 10% 以上,自 2017 財政年度僅為 610 億美元以來,規模已成長逾一倍,在2025 財政年度僑匯超過1兆美元。正如印度儲備銀行(RBI)的分析所指出的:「印度的僑匯收入通常高於印度實際流入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從而成為重要的穩定外部融資來源。」
這些資金流入已成為經濟體的關鍵緩衝,有助於彌補印度在2025財政年度高達287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僅僑匯一項就涵蓋了其中近一半(約47%)的缺口。此外,這些僑匯也有助於穩定盧比匯率、促進農村地區的消費,並在不伴隨短期資本流動波動的情況下,為國內帶來外匯收入。
這些來自新興移工國家的僑匯如今已占總僑匯金額的45%,而曾經作為印度海外勞工支柱的海灣國家,其僑匯比例正逐漸下降。
逐漸成形的新架構
近期提案的《海外流動法案》(Overseas Mobility Bill)旨在使這一全球性的流動更加制度化。該法案的制度架構相對簡明,設置了海外流動總署長、區域官員,以及由外交部(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EA)秘書長擔任主席的海外流動與福利委員會。這些機構將共同維護一個涵蓋出境勞工、外國雇主及仲介機構的中央登錄系統,並定期就海外勞動市場趨勢進行研究。
該法案亦要求建立一套整合性資訊系統,以跨國追蹤勞工動向,並為招募仲介機構制定認證規範,對違規行為處以最高達20,551美元(約2,000萬盧比)的罰款。法案甚至規劃在印度國內與國外設立勞工流動資源中心,以協助勞工並支援返國者的再融入。
為防範人口販運與非法移民,相關程序將推動資格的相互承認、為勞工提供普遍性的保險保障,並促成有關安全移民的國際協議。
隨著印度啟用 Passport Seva 2.0 新護照系統並推動數位護照的構想,一套無縫銜接、端到端的查核與制衡機制將被納入整體運作架構之中,使得防範勞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出現任何不當作為、偏差或違規行為變得更加容易。
促進國內成長
若該計畫能如預期運作,多數勞工將赴海外工作三至五年,將收入匯回國內,並最終帶著積蓄與新技能返國。如此一來,印度的僑匯便有可能演化為一個結合資本、知識與流動性的循環,進而推動國內經濟成長。
這同時也是印度將移民轉化為一種戰略的方式,將其人民塑造成全球性資產,而非經濟難民。不同於美國 H-1B 制度日益趨於限制性的發展方向,這一新模式則轉而著重於具暫時性、且對雙方皆有利的工作安排。
僑匯的流入不僅僅是資金,更是一種穩定力量。它支撐農村家庭、資助教育與住宅支出,並在出口降低時仍能維持消費動能。再加上印度蓬勃發展的軟體與商業服務收入(兩者在上一財政年度皆突破1,000億美元),這些資金流入共同構成了印度對外經濟韌性的核心。
「僑匯的流入不僅僅是資金,更是一種穩定力量。它支撐農村家庭、資助教育與住宅支出,並在出口降低時仍能維持消費動能。」
Pooran chandra Pandey, 2025 年外交部(MOFA)臺灣獎助金訪問學者。
反移民政治
然而,隨著歐洲、日本與美國等地反移民政治勢力的崛起,相關挑戰亦不斷湧現。暫時性移民方案需要嚴格的管理,以確保其維持「暫時性」;同時,如何在勞工返國後協助其重新融入社會、找到工作、創業,並將其技能加以轉移,亦將對印度的國內制度構成考驗。
但從長期的人口與經濟結構來看,整體來說似乎對印度較為有利。隨著已開發各國人口持續下降,而自動化技術仍難以填補照護與服務業的工作缺口,人力資本很可能將成為最具價值的「出口品」。
印度勞工流動與遷移的歷史
國際移民,即人口跨越國界的流動,一直是人類歷史(包括印度歷史)中持續存在的現象,並在長期中深刻形塑了印度與世界的互動模式。印度的移民歷史始於古代的貿易路線與文化交流,並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展為大規模的勞工遷移,最終形成今日遍布全球、規模龐大的印度僑民社群。
尤其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印度人積極地跨越不同地區、國家與各洲,尋求教育、就業與創業機會,並在各地建立起活躍的社群,對所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樣貌作出了重要貢獻。
根據相關證據,長期以來印度移民大致呈現出三種主要模式:其一為契約勞工移民;其二為為追求技術性與半技術性工作、教育及商業機會而進行的海外移民;其三則是近年來透過勞工流動條約發展而成,該模式並進一步納入雙邊合作架構與制度安排之中,為移民提供多元途徑,使其得以在接收國與母國皆展現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長期而言,印度的勞工流動被廣泛視為成功案例,因為印度移民在海外發展出成功的職業生涯,對接收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並形塑出具影響力的僑民群體;其分布幾乎遍及各洲,包括太平洋與加勒比海地區、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以及中東(主要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海灣國家與沙烏地阿拉伯),此外,近年來亦涵蓋日本、南韓、俄羅斯、以色列、新加坡、香港,以及現在的台灣。
一窺印度移民歷程:提供重要啟示與經驗借鑑的案例
在建構涉及印度移民的永續途徑時,若能列舉若干案例,並說明印度移民的不同模式及其貢獻,將有助於在移民歷程的分析框架中加以理解,其中包括成功的社會融入、與當地居民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在限制文化民族主義、避免移民社群形成隔離聚落的同時,仍能促成多元性、在地化與融入,以促成移民順利融入接收社會及其文化環境,並順利地在該國發展。
前往加勒比海地區與南非的印度移民歷史悠久:最早與最具影響力的案例之一
印度移民至加勒比海地區與南非始於約17世紀,最初以奴隸身分出現,但多數移民是在1860年之後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前來,主要被引入種植園工作;其後又出現所謂的「乘客型」移民,這些人主要是從事貿易與商業活動的商人。這一過程促成了規模龐大的印度僑民社群的形成,其中人口高度集中於德班(Durban),該城市亦成為印度以外族裔印度人口最為集中的城市之一。
契約型與乘客型移民(19世紀與20世紀)
契約型勞工:第一波移工浪潮始於1860年,由英屬印度將印度移工引入納塔爾(Natal),用以作為糖加工廠的勞工
這些勞工來自如清奈(Madras)與加爾各答(Calcutta)的港口,以「契約」的制度被引入,這種制度被某些人稱為「契約形式的奴隸」。
當契約結束後,很多移工會留在當地並在當地市場成為園丁或小販。
乘客型移民:始於1870年代,是那些自己負擔旅費的自由移民,主要來自於古吉拉特邦(Gujarat)和其他印度的商業族群。
這些人主要是貿易商與商人,他們建立自己的事業,並以既有的商家競爭。
鐵路擴建促進了貿易往來,帶動經濟成長,並進一步推動印度社群的持續遷移。
南非與加勒比海國家至今仍被視為印度移民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數個世紀以來,印度移民逐步與當地社群融合,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並成為當地社會與文化環境的一部分,對地方社會在社會、經濟、商業、政治、教育與文化等幾乎所有層面皆作出貢獻。鑒於印度人與南非社會長期共同發展、相互繁榮,並對地方成長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今日的印度移民往往被視為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與在地居民一同慶祝節慶、共享飲食、欣賞地方服飾與文化活動,並在宗教、商業與政治領域中彼此參與、共同領導,展現出深度融合的樣貌。
目前全球約有 300 萬名印度僑民,其中約 170 萬名印度移民居住在南非;由於外來勞工在效率提升與高等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他們使得當地人均收入提高約5%。
「目前全球約有 300 萬名印度僑民,其中約 170 萬名印度移民居住在南非,他們使得當地人均收入提高約5%。」
Pooran chandra Pandey, 2025 年外交部(MOFA)臺灣獎助金訪問學者。
美國與加拿大的印度移民:受過教育的印度人才及其對美國科技產業成長的貢獻。印度人移民美國與加拿大始於 19 世紀初,當時印度移民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與就業機會而開始定居於此。最初移民人數不多,但隨著20世紀中葉新機會的出現,其人口規模在隨後數十年間迅速成長。
截至2023年,約有300萬名印度移民居住在美國,約占美國外出生人口的6%,成為僅次於墨西哥移民、並領先於來自中國與菲律賓移民的第二大移民族群。
印度移民最初主要從事農業、伐木業與鐵路相關產業。自1980年至2019年間,美國的印度移民人口持續增加,並依據聯合國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於2019年年中所作的估計,美國已成為印度移民的第二大目的地,僅次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340 萬人),其後依序為沙烏地阿拉伯(240 萬人)、巴基斯坦(160 萬人)、阿曼(130 萬人)及科威特(110 萬人)。
印度移民是加拿大新增長期居民與移民的最大來源,根據 2021 年人口普查,其人口已超過 185 萬人,成為加拿大最大的非歐洲族裔群體。這一移民趨勢主要受到加拿大在資訊科技與醫療等產業的經濟機會、其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偏好高教育程度與豐富工作經驗人士(其中多來自印度)的計分制移民制度所推動。主要的移民聚集地包括多倫多、溫哥華與卡加利地區。
因此,經年累月之下,印度移民在美國與加拿大皆留下了足跡,並對接收國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與商業等層面的成長與進步作出重要貢獻。在美國與加拿大兩國,印度移民在學術界、醫學、新聞媒體、資訊科技產業、法律專業以及政治等多個領域中皆有傑出表現,且至今仍持續發揮影響力。
澳洲的印度移民
截至 2025 年年中,澳洲境內的印度人口已超過 100 萬人。目前,印度對澳洲的勞工流動主要是透過一項名為「青年菁英專業人才流動安排」(Mobility Arrangement for Talented Early Professionals Schemes, MATES)的計畫進行,該計畫對象為年齡介於 18 至 30 歲之間、畢業於指定大學並成功透過抽籤機制完成註冊的學士學位持有者。
目前,印度移民已成為澳洲第二大移民族群,在資訊科技、醫學與學術界等領域具有顯著存在,並對澳洲的經濟與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海灣合作理事會(GCC)國家的印度移民
印度對中東地區的勞工流動構成了全球規模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外派社群之一。雙方的歷史聯繫可向前追溯數個世紀,當代印度人在該地區的存在對經濟、文化與社會層面皆產生深遠影響。現金有數以百萬的印度人居住於中東各國,尤其集中於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並在建築、醫療保健、金融與資訊科技等產業中發揮重要作用。
印度與中東之間的聯繫可追溯至古代,透過陸路與海路的貿易往來建立。早在西元 1 世紀,印度洋的海上航線便促成了印度與中東諸王國之間深厚的經濟與文化交流。
從歷史上看,在中世紀時期,蒙兀兒帝國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維持著密切聯繫,促進了學者、商人與工匠在印度與中東之間的流動。阿拉伯語與波斯語對印度的語言與文學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印度的數學家與天文學家亦對中東地區的科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20 世紀隨著波斯灣地區石油的發現,局勢出現了重大轉變。隨之而來的經濟繁榮創造了龐大的勞動需求,吸引了大量印度勞工前往中東工作。這一移民潮在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進一步加劇,標誌著印度對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大規模勞工移動的開始。這股移動亦受到印度經濟政策的推動,政府鼓勵海外就業,將移工僑匯視為強化外匯存底的重要手段。
相關證據亦顯示,隨著時間推移,勞工流動協議有助於在各國政府之間建立互信關係,促進合作,並擴大商業與教育交流。此外,這類制度性途徑亦往往進一步發展為自由且全面的貿易協定。
在一項罕見的政策舉措中,沙烏地阿拉伯廢除了沿用 50 年、被視為落後的相關法規,透過取消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賦予印度勞工更大的工作流動自由,並放寬其勞動權利限制,包括在王國內擁有財產的權利。此一改革目前也正逐步在其他海灣合作理事會(GCC)國家中推動實施。
英國的印度人
印度人在英國的案例,無疑是一段在英國社會、政治、學術、文化,尤其是在地方經濟中逐步奠定穩固地位的精彩歷程。據估計,目前英國境內的印度人口已超過 200 萬人,而印度與英國之間的聯繫可追溯數個世紀,最早始於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時期,並由此建立起深厚的人際連結。
隨著印度人在英國社會中逐步晉升至包括經濟、政治、學術與文化等領域的高層位置,他們也順利融入英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並被視為現代英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度人在英國的存在,與其在加勒比海地區、南非與美國的發展軌跡相互呼應,皆是藉著努力、教育程度與成就而建立起的影響力。
在英國,印度企業不僅是家喻戶曉的品牌,也僱用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對英國經濟作出重要貢獻。目前英國境內有超過1000家印度企業,其中包括塔塔(Tata)、信實集團(Reliance)、辛杜賈集團(Hinduja)、埃薩爾(Essar)、安賽樂米塔爾(ArcelorMittal)、雷迪博士實驗室(Dr. Reddy)等知名企業,合計在英國僱用超過12萬6千名員工。
印度與英國亦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雙向貿易與商業往來鋪設更高層次的合作道路,並在雙邊貿易協定架構下,將勞工流動納入協議的一環。
從全球範圍來看,印度勞工流動的整體趨勢及其僑民在多個層面與層級所作出的貢獻,也值得進一步關注,特別是在更接近印度本身的地區情境下:例如部分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雖然相對富裕、國土規模較小,卻正面臨人口快速老化與出生率下降的雙重挑戰,其年輕世代一方面對本地勞力密集型產業興趣不高,另一方面則更傾向於透過高等教育與海外就業,尋求更具吸引力的發展機會,因而對印度勞工的需求日益增加。
新加坡與印度移民
新加坡一直被視為該地區最為進步的國家之一,其發展建立在吸納外籍人士、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以及企業對企業連結所帶來的優勢之上,並透過設計財政誘因、公平且透明的簽證制度,以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來吸引人才。印度人正是這套制度的受益者之一,目前約占新加坡總人口的7.6%。現今約有 80 萬名印度人居住在新加坡,包括學生、永久居民及其他非居民身分者。
居住於新加坡的印度人從事的產業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資訊科技與科技產業、金融與銷售、銀行業、旅宿與餐飲服務、一般與技術性工種、客服服務以及教育等領域。
新加坡常被稱為建立在教育實力、外籍專業知識與多元勞動力基礎上的自由經濟體,並持續作為多元勞動力成功融入在地社群的典範,彼此融合自然,如糖與牛奶般密不可分。作為一座國際化城市,新加坡亦因工作便利性、生活品質,以及公平透明的制度等因素,逐漸成為專業人士的首選目的地。
推動在即的勞工流動條約
印度-日本人才夥伴關係
作為深化經濟合作的重要一步,印度與日本宣布推出一項全新的「人力資源交流與合作行動計畫」,目標是在未來五年內促成超過 50 萬人次的雙邊人員交流。
該計畫的重點之一,是預期將有約 5 萬名具備技術與半技術背景的印度專業人士前往日本,涵蓋資訊科技、數位轉型、先進製造、半導體、交通運輸、研究與創新等多個產業領域。
此一倡議旨在回應日本不斷變化的人才需求,同時為印度具全球競爭力的技術勞動力開拓國際職涯發展途徑。
雙方合作的重點領域包括:技術型勞動力的流動與招募、產學合作、語言與文化培訓計畫,以及創新、數位經濟與永續發展夥伴關係。
這項舉措反映出印日戰略與經濟關係正快速深化,並與未來勞動力與科技發展需求高度契合。
印度-南韓流動條約
印度與南韓正就簽署一項移民協議進行磋商,以促進兩國專業人士之間更為便利的流動。此一協議有望加強印度與南韓兩大高科技生態系之間的合作。
該項安排預計將透過政府既有的移民機制完成,這也使其不同於印度先前與英國、德國及澳洲所簽署的較為全面性的移民協定。移民協議有助於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同時也協助印度專業人士在科技、汽車等多個領域赴海外工作。
南韓高品質的教育體系使其成為具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根據外交部的資料,目前約有 12,000 名印度人居住於南韓,其中約 300 人為印度裔。大量印度學生正在南韓攻讀研究所與博士學位,主要集中於基礎科學領域。此外,資訊科技、航運與汽車產業的專業人士亦有不少移居南韓。
不僅是南韓,印度也正尋求與台灣及其他國家建立移民協議。印度已與日本簽署類似性質的協議,其中的「特定技能勞工制度」(Specified Skilled Workers, SSW)允許勞工在包括漁業、汽車維修與建築等 14 個領域中赴日工作。
印度與俄國的勞工流動條約
印度與俄羅斯預計將在今年 12 月於新德里舉行的年度高峰會期間、配合普丁總統對新德里的正式訪問,完成一項勞工流動協議,以保障在俄羅斯日益增加的印度勞工之權益。該協議亦將有助於在未來數年內提升印度人在俄羅斯的就業人數。
面對人口持續下降的情況,俄羅斯極欲擴大其勞動力中的印度勞工比例。目前,印度勞工已在建築與紡織等產業中找到工作,而俄羅斯對機械與電子等領域的技術型勞工需求亦正持續上升。
根據俄羅斯勞工部所設定的配額,至 2025 年底,將有略高於 7 萬名印度人在俄羅斯就業。印度勞工部與俄羅斯相關部門已就此議題展開討論,並期望能儘快達成正式的勞工流動協議。
隨著印度僑民社群的持續成長,其未來可能成為印俄夥伴關係的重要支柱,同時也將推動雙邊經濟合作。今年印度自俄羅斯進口的鑽石與黃金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今年8月,俄羅斯對印度的鑽石出口額攀升至3130萬美元,較2024年8月的1340萬美元增加逾一倍。然而,今年前八個月俄羅斯對印度的鑽石供應總量卻下降近 0%,降至3421億美元。
俄羅斯是全球最大的毛鑽生產國,歷來亦是印度龐大鑽石切割與拋光產業的重要供應來源之一。然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鑽石貿易及其最大採礦公司阿爾羅薩(Alrosa)所施加的制裁,已對印度相關產業造成影響。
此外,印度鑽石產業亦正面臨美國對切割與拋光鑽石課徵 50% 關稅所帶來的挑戰,其中包含因印度採購俄羅斯石油而加徵的 25% 懲罰性關稅。
新德里與臺北的勞工流動途徑
在臺灣人口快速老化與出生率持續下降這兩項因素的推動下,臺北與新德里有意簽署一項勞工流動協議,以因應特定產業領域的人力短缺,並引進印度勞工填補臺灣的勞動需求。相關準備工作已隨著必要的備忘錄簽署而展開,後續將透過取得所需核准、建立相關作業程序,並完成包含立法審議在內的正式批准程序。
為進一步推動此一進程,台灣與印度已就勞工流動協議的理解與實際落實展開討論,並致力於排除任何可能的障礙,以確保協議能順利推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與印度已於 2024 年 2 月 16 日完成一項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以促進印度勞工在台灣的就業。
該協議由駐印度臺北經濟文化中心代表,以及印度—臺北協會駐臺北總幹事簽署。雙方目前正就協議細節進行研議與磋商,包括可能引進的勞工人數,以及印度勞工所需投入的產業領域等關鍵議題。
近年來,臺灣與印度在文化與教育、投資與貿易、科學與技術,以及醫療與公共衛生等領域持續擴大合作。隨著夥伴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勞工流動協議亦將有助於減輕台灣人口老化與出生率下降對勞動力所帶來的衝擊。
勞動部(MOL)對此備忘錄表示歡迎,並指出此舉是為回應台灣在農業、建築與製造業,以及照護產業中日益嚴重的人力短缺問題。
勞動部亦肯定印度勞工已在歐洲、中東與亞洲多國勞動市場中的參與情形,並指出日本與南韓也正規劃邀請印度勞動力前往其國內工作。
依據相關安排,勞動部將負責進行嚴謹的評估,以確認人選具備一定的教育程度與良好的英語能力,並將先行推動小規模試行計畫,在評估成效後再進一步招募更多來自這個南亞國家的勞工。
目前臺灣約有5000名印度人,其中約3000人為在學學生,其餘則包括企業經營者、藍領勞工、智庫研究人員與學者,以及資訊科技與軟體等專業人士。鑒於印度與臺灣正積極推動在文化與教育、半導體與資訊科技領域的貿易與投資合作,並持續深化產業對產業以及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未來選擇台灣作為求學、就業,特別是在資訊科技、軟體與醫療領域發展目的地的印度人數,預期將持續增加。
臺灣的新南向政策已帶動來台就讀的印度學生人數上升,而一旦勞工流動協議作為更全面合作安排的一部分正式簽署,相關成長動能預料將進一步加速,這種全面性安排亦包括貿易、商業、投資、觀光、較為寬鬆的簽證制度與獎學金措施等,正如許多國家與印度既有的合作模式。
此外,未來亦可預期印度與臺灣將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將勞工流動協議納入此一全面合作與夥伴關係架構之中。透過在雙邊合作與協議中嵌入勞工流動機制,作為促進印度人更便利移居臺灣的管道,印度與臺灣雙方皆可從中獲得更多利益。
「未來亦可預期,印度與臺灣將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將勞工流動協議納入此一全面合作與夥伴關係的安排之中。」
Pooran chandra Pandey, 2025 年外交部(MOFA)臺灣獎助金訪問學者。
全球需求與印度的勞工供給鏈:隨著全球即將面臨大規模勞動力短缺,已開發經濟體紛紛加緊填補勞力缺口。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一項研究估計,到2030年,全球將出現約 4500 萬至 5000 萬名勞工的短缺,相較之下,2023年的缺口僅約為500萬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開始挺身而出。普遍且務實的看法認為,印度有可能在 2030 年前將其每年的勞工「出口」規模加倍,從目前約 70 萬人提升至 150 萬人。
德國與日本正站在這一轉變的最前線,積極地招募印度人才。根據《紐約時報》(NYT)的報導,在印度國內,德國與日本最受關注,前者被視為進入歐洲的門戶,後者則是通往東亞的入口。芬蘭與台灣亦已與新德里簽署勞工流動相關的備忘錄,並正持續推動將其制度化的討論。
相對地,如同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英語系國家則早已為印度技術勞工建立渠道,並不需要依靠政府的安排。
印度外交部長(EAM)蘇杰生(S. Jaishankar)已將這些夥伴關係置於印度外交與軟實力策略的核心位置。去年 12 月在印日論壇上,他甚至將「勞工流動交流」的重要性置於國防合作與半導體供應鏈之上。至今年 8 月,兩國已推出計畫,每年向日本派送 5 萬名印度勞工。
在國內層面,緊迫性同樣十分明顯。儘管印度經濟快速成長,其 GDP 規模如今已與德國、日本相當,但創造工作機會的速度卻未能同步跟上。
自疫情以來,約有5000萬名原本在製造業或服務業工作的印度人被迫回流至農業部門,對於那些期望進入全球技術型勞動市場的人而言,這無疑是一種退步。
臺灣與印度攜手共舞的時候到了
隨著台灣與印度在制度層級上逐步推進相關努力,雙方可就此一行動保持務實態度,並尋找不僅能善用印度勞工資源的可行途徑,這支勞動力在過去數十年間已在主要經濟體中證明其價值與實力,同時亦是僑匯匯款的重要來源,並逐步轉化為軟實力資產,使接收國成為真正多元的社會。此類努力亦往往最終促成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以及國家之間更深化且具戰略性的夥伴關係。
然而,這樣的協議並非輕易可成,仍需克服區域狀況、相互制衡的力量、制度設計與方法、結構、互信,以及緊迫時程等多重挑戰。理想情況下,相關工作應在最高政治層級推動,並同步搭配雙邊較為開放的簽證制度、納入教育與研習計畫,以及為受過教育的印度人才設計漸進式發展途徑,使其能將台灣視為求學與日後就業的優先選項;尤其是在俄羅斯、日本、南韓等國正積極尋求與印度政府簽署勞工協議的背景下,更顯其時效性。同時,也不排除未來某個時點,印度較為自由的勞工協議制度可能因調整需要而變得更加嚴格或是暫時寬鬆。
證據顯示,此類發展之所以能成功,往往建立在各國長期累積的互信與理解之上。唯有新德里與台北在當代情境中加以學習並調整,這些經驗才能發揮作用。這些協議不僅僅是勞工協議,更是深化相互理解與建立長期善意的重要基礎,並為雙方帶來深遠而廣泛的利益。
在臺灣人口快速老化、出生率持續下降,而印度同時擁有可供應的高技能、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之際,這樣的合作對雙方而言是雙贏。不僅能把握現有機會,也能在亞洲乃至整個印太地區,完成更宏觀的合作夥伴關係布局,以強化區域合作,而這正與臺灣的新南向政策所體現與提供的方向相呼應。
對印度而言,臺灣這個近鄰亦能在半導體、商業與投資,以及科技等領域,補充並強化其崛起動能,並進一步拓展至紡織、運動用品、礦物加工與自行車製造等產業的合作,從而在勞工流動協議及其衍生效益上,形成穩健的雙向發展軌道。
未來展望
若印度的勞工流動架構能依計畫順利落實,納入協議的勞工可在不改變國籍的情況下,赴海外工作三至五年。其目標並非永久移民,而是形成一種循環流動 — 將資本、國際經驗與技術知識帶回國內,並隨時間推移,逐步重塑印度的本土經濟。
20世紀的關鍵在於石油,相對地,21世紀的關鍵很可能在於勞工,而印度似乎擁有比任何國家都更多的勞動人口。這是一項明確的優勢,不僅能透過遍布 G7、G20與印太地區的強大印度僑民社群,形塑印度的軟實力,也能藉由持續的僑匯流入,帶來長期的經濟貢獻。
其核心邏輯相當簡單:印度擁有充沛且年輕的勞動力,而多數已開發國家則因人口老化與出生率下降,正面臨年輕勞動力不足的困境。若能以負責的方式,將這兩端的供需面向加以合理連結,雙方都將從中獲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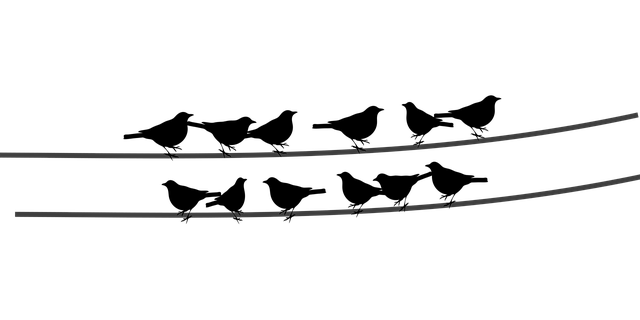
Pooran Chandra Pandey 現隸屬於臺灣(R.O.C)政府下的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並常駐於臺北。他目前致力於推動臺北與新德里之間的勞工流動協議,以及區域合作的外交軟實力。根據此協議,臺灣同意在尖峰時段逐步引入最多10萬名印度人,於特定產業就業,並由印度政府提供職業培訓。同時他也致力於深化臺北與新德里的雙邊關係,進而促進兩國關係與區域合作。
本篇文章觀點屬於本文作者,並不代表本刊《印太政治》的立場。
